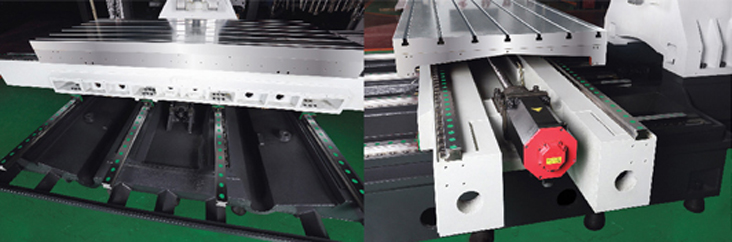产品详细
2015年7月17日10时许,被害人将放有2万元现金的信封遗忘在银行填单台上,随后在填单台视线范围内的银行等候区座位上低头看手中的读物。正等候办理业务的被告人周某某看到填单台上有一信封,悄悄确认内有钱款后,将信封藏入自己的包内并离开。10时30分许,仍在原地的被害人发现钱款丢失,但无法想起具体丢在何处,在银行四处寻找未果后报警。同年7月29日,民警至周某某的住处询问,周某某承认在银行捡到人民币2万元, 并于8月3日通过派出所将2万元归还被害人。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某因一时贪念,在银行大厅内拿走他人遗忘的钱款,该行为虽有违中华民族拾金不昧的道德风尚,应予谴责,但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遂判决周某某无罪。一审宣判后,检察院提起抗诉,二审法院认为, 周某某非法占有的被害人一只装有现金的信封, 系被害人丢失的遗忘物,不是被害人或银行有关人员控制或占有的财物,周某某没有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获取财物,不能以盗窃罪认定,遂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涉案财物(被害人遗忘在银行填单台上的现金)是否属于遗忘物?如果认为涉案财物仍处于他人的占有之下,则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其取走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如果认为涉案财物属于遗忘物,则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将遗忘物非法据为己有,不构成盗窃罪,此时由于被告人后来通过公安机关将涉案财物返还给被害人,不满足侵占罪“拒不交出”这一要件,也不构成侵占罪,因而只能按无罪处理。
本案中,一审法院得出了无罪的结论。公诉机关抗诉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应成立盗窃罪。主要理由包括:(1)银行是从事金融服务的特定场所,对外开放公共性有限,同时银行内有保安人员等安全措施,在银行内短暂离开身体的财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2)被害人主观上始终未放弃对该财物的控制,且填单台与等候区座位距离近,涉案财物脱离被害人的时间短,当时办理业务的人数极少,能够认定被害人仍就保持对该财物的占有;(3)被害人的一系列举动,均在被告人近距离视线范围内,且当时等候区只有三人,被告人应当知道装有现金的信封可能是被害人失落,但被告人不进行任何询问、核实就迅速将涉案财物藏在包内离开银行,被告人实施的行为不是公开捡拾,而是秘密窃取。
对此,二审法院认为,盗窃的对象应当是他人实际控制或占有的公私财物,其特征是,他人在客观上已经对财物实际控制或支配,在主观上已形成了控制或支配财物的意识,本案中涉案财物不符合上述特征,故对被告人的行为不能以盗窃罪论处。主要理由包括:(1)被害人未想到自己将涉案财物遗落在填单台上,发现涉案财物丢失后,也无法回忆起丢失的具置,其已经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2)银行虽然属于公共场所,但并无监管顾客遗忘物的义务,且银行工作人员始终未曾发现或者意识到在填单台上有遗忘的涉案财物,缺乏控制、支配的意思,不能认定银行对于涉案财物存在第二重占有;(3)被告人虽然在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也实施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但其非法占有的财物属于遗忘物,故对其行为不能以盗窃罪认定。
占有是财产犯罪的核心课题,根据财物是否被他人占有(占有的有无),可以区分盗窃罪与脱离占有物侵占;根据财物是否被行为人占有(占有的归属),可以区分盗窃罪与委托物侵占。下文在介绍相关学理的基础上,对本案的裁判理由来探讨。
民法和刑法都使用占有概念。民法上的占有,是指民事主体控制特定物的事实状态。刑法上的占有同样强调主体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关系,但刑法理论一致认为,刑法上的占有不同于民法。被民法承认的间接占有、占有继承等观念上的占有类型,在刑法上均不属于占有,而民法上的占有辅助人则可能基于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而在刑法上具有占有。在财产犯罪中,不能根据《民法典》中关于占有的规定来判断占有的存在和归属。
那么,怎么样来判断是不是真的存在刑法上的占有呢?显然,事实因素是认定占有的核心,当主体对物具备物理上的控制,且排除他人的干涉时,肯定占有的存在并无疑问。典型的例子如拿在手中的皮包、放在脚边的行李箱等。然而,单纯按照事实上的支配关系来认定占有,对那些和主体在空间上联系较弱的物,如长期旅行在外的人家中的财物、停在路边的自行车、农夫遗忘在田间的农具、随处跑动的宠物等,很难认为存在很明显的事实支配,但此时若否定占有的存在,则与社会观念不符。有鉴于此,德国、日本的通说均主张应当在占有概念中引入社会—规范的因素,主体对于某物的事实支配(拿取可能性)越强,就越不需要要求“社会上对于此支配的承认”;反之如果社会上对于某人对某物的支配的承认越强,事实上该物的拿取可能性就可以越弱。此外,刑法中的占有虽然也要求占有意思,但其只是一种自然的、事实性的支配意志,在大多数情形下仅对认定客观上的事实性支配起补充作用。即使是儿童和精神病患者也具有占有意思,当占有者对一些范围内的物品具有概括的占有意思时,即可能够认定其对该范围内的全部物品具有占有意思,而无须对每个处于该范围内的物品存在认识。
据此,认定刑法中的占有,首先应当考察事实上的支配是否明显,当事实上的支配减弱时,则须结合规范性的因素对占有进行补强。只有主体在社会一般观念下,完全丧失对物的事实支配,或者完全缺乏占有、控制财物的意思的,才能否认占有的存在。具体而言,存在以下几种类型:(1)处于某人的事实性支配领域内的财物,即使没有处于持有或者看护状态,也为其所占有;(2)即使处于某人的支配领域之外,如果能推定存在该人的事实性支配,也可以认定占有;(3)作为特殊情形,对于有回到主人身边习性的动物(猎犬等),也可认为他人的事实性支配延伸至此;(4)某人即使失去了对财物的占有,若该财物已经转移至建筑物的管理者等第三人的占有之下,则仍旧能肯定占有;(5)行为人主观上明确有抛弃、放弃占有的意思,或者忘记财物所处位置,且时间、空间距离较大的,应当否认占有存在。
本案中,被害人将涉案财物遗忘在银行填单台,其对财物的事实支配属于削弱的状态,此时如果严格按照事实性支配的标准,似乎可以认为其已丧失了对涉案财物的占有。然而在本案中,被害人当时距离填单台并不远,随时都有想起财物丢失,或者发现涉案财物的可能。在这种(事实性的)占有陷入松弛状态的场合,如何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来确定被害人是不是已经完全丧失了占有,就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
对此,日本最高裁判所在1957年的判例中是以被害人自遗忘物至想起财物丢失后,折返回来寻找财物之间的间隔时间(5分钟),以及从忘记财物的地点与折返地之间的距离(约19.58米)作为判断材料,进而肯定被害人的占有;而在2004年的判例中,最高裁判所未强调被害人想起财物丢失而折返这一事实,而是强调在被告人获取财物的时点,被害人与财物之间的距离(约27米),进而肯定被害人的占有。在笔者看来,后一个判例更具参考价值,因为被害人是不是真的存在占有的判断时点,应当与被告人的实行行为相一致,被害人究竟何时想起财物丢失,以及此时距离财物的距离,并不是应当重点考察的因素。因此判断被害人是否对涉案财物存在占有,就是要判断在被告人取得涉案财物时,被害人与涉案财物在时间和地点上的接近程度,以及被害人恢复事实性支配的可能性大小。
本案中,当被告人获取涉案财物时,涉案财物就在被害人的视线范围内,只要被害人意识到财物丢失,就有能力随时恢复事实性支配。虽然后续案情表明,被害人并未想起具体将涉案财物丢在何处,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时被告人已将涉案财物取走。因此,只要将占有的判断时点确定为被告人实施行为时,并且从规范的层面考察占有关系,就应当肯定被害人对涉案财物仍然具有占有。
更重要的是,即使认为被害人已经丧失了对涉案财物的占有,也不能贸然认为涉案财物属于遗忘物,而是要继续讨论占有是否被转移至场所的管理者(银行工作人员)。这是由于,排他性地对一定场所进行支配者,对处于该场所内的财物也存在占有。对此有观点认为,如果承认银行可能对顾客的财物存在占有,那么公民进入银行后所携带的财物自然就成为银行有关人员控制或占有下的财物,该财物一旦灭失,银行或者工作人员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相应的责任,这显然不合理。然而,一旦引入规范的视角,前述担忧即可迎刃而解。德国刑法理论认为,占有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观念下的“禁忌领域”,其意味着除占有人外,其他人不得随意地碰这样的一个东西。被社会承认的占有领域,首先包含房屋和住宅,其次包括个人本人、其身着之衣物以及随手所拿的物品,在占有领域内的财物,一概由该领域的主人所占有。此时领域的主人只需要具有概括的占有意思即可,无须考虑具体占有了哪些财物。而在顾客贴身携带财物进入银行的场合,虽然财物进入了银行的占有领域,但由于其原本处于顾客的占有领域内,从而形成了一种占有领域的重叠,即“占有飞地”,在这种情形下,占有的归属取决于对占有领域背后的社会观念的衡量,此时对银行这一公共领域的尊重,要让位于顾客的身体隐私,故只有在财物脱离顾客身体领域的场合,才会转由银行占有。
判断场所管理者对财物的占有,需要仔细考虑场所的封闭性、排他性程度。一般认为,在旅馆、银行、浴室、出租车等场所,通常应肯定被害人遗失财物后,对财物的占有转移至场所管理者。而在大型超市、大型餐厅、正在行驶的列车等场所遗失物品的,则不能肯定占有的转移。总之,对于是不是真的存在占有,要根据具体的案情进行判断,即使是在餐厅或者咖啡馆的座位上的遗忘物,根据该餐厅的管理情况及客人的入店方式等,其结论也可能不一样。本案中,在被告人取得涉案财物的时点,即使认为此时涉案财物已脱离了被害人的占有,但从其位置(银行填单台)、外观(装在信封内),以及当时等候区只有三人等因素看,也足以肯定涉案财物的占有转到了银行管理者之下,至于银行工作人员是否现实地发现或者意识到在填单台上有他人丢失的财物,亦不影响占有的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中涉案财物不属于遗忘物,被告人构成盗窃罪。
本案集中反映出理论和实务在占有问题上的理解差异。在笔者看来,法院的裁判思路很可能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1)将占有理解为纯粹的事实概念,在占有松弛的场合,容易忽略占有的规范性因素,而径行否认占有的存在;而在占有转移的场合,则会要求场所管理人具有现实的占有意思。(2)将占有的判断时点后置至被害人发现财物丢失时,导致过度纠缠于被害人无法回忆起财物位置这一事实。(3)将传统刑法理论中的遗忘物概念作为大前提,在占有松弛的场合,考虑到涉案财物确实是被害人“忘”在填单台上的,进而得出属于遗忘物的结论,而忽视了遗忘物本质上属于未被他人占有的物。这些认识源自日常语言的陷阱,而忽略了占有的规范性,是值得反思的。
本书以刑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结合阶层犯罪论的逻辑和理念,精选100个典型刑事判例,并对判例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深入说理,对不同的学说进行梳理论证,注重建立刑法学说与案件处理之间的紧密关联。
本书致力于缩小理论与实务之间的距离,注重客观性思考、体系性思考和功能性思考的同步推进,通过对我国司法机关实际处理的大量案件做多元化的分析和评价,熔前沿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于一炉,为刑法研究者按照刑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有关问题指引研究方向。同时,为司法实务人员提供更严谨的分析思路,得出妥当判决结论,以改变判决依赖司法解释的现象,使司法实务人员树立罪刑法定、刑法谦抑、人权保障等基本理念,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
本书以专题为经线,以问题为纬线,较好地将案例分析和理论叙述相结合,完整地呈现刑法总论的基础原理。可以说,《案例刑法研究(总论)》一书是刑法案例类著作的升级版,对于直观和生动地掌握刑法基本理论具备极其重大参考价值。本次修订,针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进行了调整,并增加了指导案例。